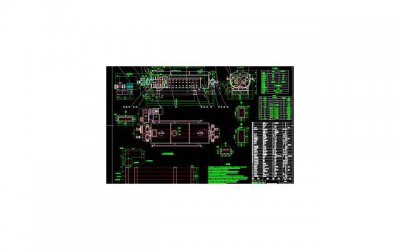大陆第一位玛莎·葛兰姆舞团首席舞者,她怀揣着一个被震醒的梦

采访:阿钟、偷你牛
作者:阿钟、偷你牛
辛颖从纽约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敲北京舞蹈学院的门,毛遂自荐要在那当老师。
她那时候 28 岁,已经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但比起二十出头更该横冲直撞、梦比天大的年岁,28 岁的辛颖的确要更自信、更有冲劲,她对着给她开门的张守和老师噼里啪啦自报家门,对方甚至没反应过来。
张守和是北京舞蹈学院现代舞中心主任,也是舞蹈学院现代舞学科创始人之一,留校任教二十余年,曾在多国留学、演出,但从没听说过辛颖这号人。
敢贸然去敲门,辛颖自然做好了准备,她那时候早已被玛莎·葛兰姆舞团的核心一团正式录用,再过不久她将会随团回国演出,成为舞团在国内推广的代表。那次演出,舞团带来了玛莎·葛兰姆始于 1930 年代的三部经典原作,辛颖在《深沉的乐曲》中独挑大梁。
巡演结束后,辛颖正式晋升为玛莎·葛兰姆舞团首席舞者。
这是一份备受瞩目的成就,作为现代舞最早的创始人之一,玛莎·葛兰姆创建的舞团被称为“美国宗师级现代舞团”。创立至今的 90 多年里,能晋升到首席的华人舞者屈指可数,而辛颖是中国大陆第一个解锁这一成就的舞者。

辛颖坐在我们面前,瘦削、高挑,但整个身体充满了力量感,她说话的时候会习惯性以舞蹈动作来演示、讲解,一动起来,手臂上的肌肉立刻显出线条。
她跳舞已经二十多年了,从五岁开始生活就跟舞蹈紧密相关,那时候别的小孩被逼着上兴趣班,总免不了呆滞、掉眼泪,充满了不情愿,只有辛颖上课时总是很开心。她开心,母亲也开心,总算给爱活蹦乱跳的女儿找到个合适地方了。
她跟母亲生活在东北,每个周末母亲都要带着她去舞蹈班上课。全中国的少儿舞蹈班大概都大同小异,一间教室、一位老师、三四排小朋友,每个小朋友在老师的指令下做动作,不用知道为什么,动就行。

辛颖回忆起小时候学舞的这些经历,脑海里最先冒出来的就是老师的一句“大汽车刚停下”。虽然不常深究舞蹈背后,但在这种肢体摆动里,辛颖依然获得了很多快乐,在母亲的督促下,她不断考级年仅十五岁就考取了南京艺术学院。
15 岁的女孩要去念大学,做母亲的当然开心又不放心,于是母亲决定把家从东北搬到南京。在南京的生活跟在东北的没什么不同,只是气候潮湿了一些;大学生活跟以前的日子也没有太大不同,仍然是练舞、比赛、休息。
没什么不同的日子也有结束的时候。四年后 19 岁的辛颖从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同时获得了一份去四川绵阳的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当老师的机会,19 岁还在跳舞的女孩,下一秒就成了老师,带着一教室的学生在排练室里重复她重复过无数遍的日常。
这种日常为辛颖编织了一个安稳又相对封闭的世界。
绵阳地处四川盆地西北缘,有一条涪江纵贯全市,作为科技城,在中国城市里有一些不大不小的认知度,在这里的生活知乎上有人概括过:“是真的想一辈子在这里安家 ,城市不大不小、空气优良、中小学教育资源很不错、周边县市风景也好。”
几句话就能描绘出舞蹈老师辛颖的一生。更何况,除了稳定的工作,她还有一位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的男朋友,两人同为东北老乡,男友也颇得母亲赞许,如果不出意外,辛颖的一生大概就如那几句话一样,平稳顺遂。

意外发生在一个全国人民都熟知的时刻,2008 年 5 月 12 日。那次震动给整个国家都留下了印记,对辛颖来说,这道印记要更直观、鲜活、触动人心。
绵阳市距震中汶川仅一百多公里,地震发生那天,辛颖的母亲上山拜佛了。那是一段让人措手不及并且无法思考的经历,整片土地的人都处在懵懂又惊慌失措的情绪里,人们好像被抽进了真空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空白。
辛颖想办法跟母亲取得了联系,确保安全,那时候绵阳市中心医院在找志愿者,辛颖去了医院帮忙。亲人安好的庆幸还来不及涌起,她看到了更疮痍的世界。
医院大厅已经被淹没了,被担架、门板和受伤的人群,从大厅里过必须得踮着脚尖。辛颖在 CT 室帮忙,有母亲带着孩子来做检查,小孩的头被硬物砸到肿胀,整颗头像礁石一般;有满身尘土的父亲带着女儿来,检查的过程中辛颖跟他聊天,问家里人都还好吗,对方平静地回答“还有个孩子,找不到,应该没了”。
检查完父亲拉着女儿就走,紧紧拽住,“就那时候你什么都顾不得了,能抓到一个是一个。”
这种巨大的、可触摸的群体伤痛在辛颖心里留下了划痕。震后重建,辛颖回到学校继续当老师、跟着舞团到处做答谢演出、准备各类参加比赛的舞蹈,“但心里就有一股劲,想做点什么,只是当时想不出来”。
电视里永远播着地震新闻、灾后新闻;她去参加的比赛、演出里,舞团永远跳着慰问灾区群众、激励人奋发的舞蹈,以至于她编出的一支青涩、有生命力但慰问意味不那么重的《青苹时节》在拿奖后也受到质疑:
你们从四川出来的舞团怎么不做“灾后大爱”?
辛颖很想告诉所有人,“正是因为我们身在其中,经历过这些,所以才无法一遍又一遍让自己沉浸在这样的氛围里。”

(图片出处:玛莎·葛兰姆舞团剧照)
跑了一年多这种充满形式感的演出,辛颖感受到她对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事物的渴望。她想起大学的时候,有一位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来教授现代舞课程,课上老师只教发力点、肌肉收缩和身体松弛等,动作则完全让学生用情绪自由发挥。
那是辛颖第一次接触到现代舞,第一感觉就是酷,原来比起从小学到大的柔美中国舞还可以有酷的舞蹈。现在,她想起了那种感觉,那种自由支配自己身体,感受到其中迸发出力量的感觉,她想起了老师讲现代舞历史时提起的那个名字,“玛莎·葛兰姆”。
她知道她要去做点什么了。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的领导是好领导,或者说,他们也被震醒了。
辛颖去领导办公室提出想出国学习的时候,其实自己都没太搞明白,具体去哪、学什么,领导问起来,她也只能先回答“去美国,学现代舞,那里有最顶级的玛莎·葛兰姆舞团”,没想到对方听完很痛快就答应了,“你能申得上,就去。”
“我当时当真了”,花了半年时间,辛颖联系玛莎·葛兰姆舞蹈学院、递交各种申请资料、准备签证,瞒着母亲和男友搞定了一切。那时一切都还在重建,一个三四线城市没有名气的学校,愿意送一位普通教师出国学习,这种机会只有一次。
但母亲并不能理解这个机会的珍贵,她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在跟女儿二十多年的相处里,母亲的人生跟女儿是绑定的,她们从东北搬到南京,再从南京来到四川的这座城市,看着女儿长大、成为老师、交了男朋友,生活轨迹本来应该这样继续顺延。

(玛莎·葛兰姆在舞蹈房教授学生们舞蹈动作)
就在生活逐渐恢复秩序,女儿可以跟男朋友谈婚论嫁的阶段,她突然说要去美国学跳舞,还是去跳她根本没听过的舞。玛莎·葛兰姆即便再有名气,在辛颖的母亲这里都是 0,她无法同意女儿的这个决定。
但辛颖并不打算回头,她跟母亲因为这件事发生过很多争吵,两个人僵持不下,学校已经开会同意让她去美国,第一年的学费也承诺会负担,辛颖想着,用缓兵之计,告诉母亲自己只呆一年。

(摄影:Jacob Jonas)
她终于如愿出国了,以“结了婚再走”为代价。
2010 年,辛颖在纽约。语言不通、饮食差异、没有朋友、想家……这些都还能忍受,更大的打击来自于学业上。因为语言不通,辛颖每堂课都只能听个大概,后来分级考试她被分到了 0 级,上课的时候老师教动作,她怎么也做不对,只能长时间泡在舞蹈室里。
对自己专业能力质疑的同时,辛颖还面对来自家人的压力。纽约跟国内的时差正好 12 个小时,白天在学院练舞精疲力尽,晚上回家还要面对母亲的催促和追问,“不听话、乱来、没前途”这样的指责时不时会出现。
最大的争吵爆发在第二年,那一年辛颖考上了玛莎·葛兰姆舞团二团,并且拿下了奖学金,这意味着她可以继续在美国学习。她打电话回家,电话那头的母亲情绪崩盘了,劝到最后母亲整个人失控,接连质问她“是不是就要跟我作对!”
更让母亲无法接受的事辛颖没有说,她想结束自己与丈夫的婚姻关系。
“我那时候根本不懂爱情,在舞团里跳舞,红色、黄色、白色,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情感状态,热烈的、雀跃的、纯洁的,我都体会不到。”到纽约半年后,辛颖就有了想结束这段关系的念头,但她始终没有说出口。
长久以来跟母亲相依为命,在舞蹈世界里成长,她其实很少关注自我,来到纽约开始独自生活求学后,辛颖才感受到了变化。
周遭的西方价值观冲击着她,虽然老师给她支招,让她告诉母亲“我很爱你,但我有我自己的人生”,在她看来是与东方传统格格不入的处理方式,但她也不可避免有了这种意识。
离家愈远,辛颖反而有了对抗的勇气。两年后,她跟丈夫结束了这段婚姻。

红色代表热烈、黄色代表雀跃、白色代表纯洁……那支舞叫《天使游戏》。辛颖拿到了红色天使的角色,从这个角色开始,与她对自身思考认知一起成长的还有她的专业能力,到 15 年舞团回国巡演的时候,辛颖已经能够在《深沉的乐曲》里独挑大梁了。
这支舞是玛莎·葛兰姆 1930 年代的作品,那次巡演舞团带了三支经典原作,在国内的演出颇受瞩目。辛颖在台上跳,母亲在下面看,演出结束各家报道纷涌而至,母亲看到女儿的名字跟那些眼熟的舞蹈家沈培艺、杨丽萍放在一起,隐隐约约意识到“女儿的决定好像是对的”。

(辛颖在雅各布之枕舞蹈节上表演《悲歌》,摄影:Chris Jones)
与母亲的和解来得很自然,巡演结束后回到纽约,辛颖正式被提升为玛莎·葛兰姆舞团的首席。
距离她到美国已经过了五年,辛颖在而立之年长成了。升为首席的第二年,辛颖与在北京相识的爱人结婚,《青苹时节》的那颗青涩果实终于遥遥落地,她懂得了各种颜色的滋味。
但人的成长并不会就此停滞,首席在一个舞团里仿佛是金字塔尖的存在,曾经在玛莎·葛兰舞团里跳到首席的舞者也无法在技艺或舞蹈这件事本身上更进一步,辛颖有了新的问题,“人生是条很长的路,在这之后,我辛颖又是谁?”
这一次她有比当年更明确的答案,玛莎·葛兰姆技术和现代舞在国内的认知度并不高,但这一鼓励舞者感受内心情绪、充盈满生命力的舞蹈值得被更多人认识,而国内专门教授玛莎·葛兰姆技术的人并不多。
在国外的时候,辛颖明白自己的文化背景和舞蹈训练背景和别人都不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可以成为和别人不一样的舞者”,回到国内,她也不由会问“我到底是谁,我的风格是什么,我除了提供葛兰姆技术和精神之外还能有什么?”

(辛颖出席中美建交40周年活动照片)
敲开北舞的门只是第一步,从 13 年之后,她就成为了北京舞蹈学院的客座教授,每次回来都会到北舞上课;在上海她开办大师班与训练营,有邀请她参加关于现代舞活动的,她都认真对待。
在北京、上海这些有现代舞学科基础的地方,辛颖对玛莎·葛兰姆技术的推进还不算难,只是时常会遇到“这个技术是不是老了?”这样的质疑,更难的地方在她回到老单位任教以后。
出于对感恩、回馈,也出于推广现代舞的心理,辛颖回到老学校,在当地舞者反对与不理解中组建了一个现代舞团,每一个来跳舞的人都会问她,“学了这个舞蹈也不知道以后能做什么,为什么要学?”说得直接一点,开培训班也没人来。
辛颖只能一次次沟通,让对方理解现代舞与中国传统舞蹈的区别、解开人们的误解。
在艺术教育和鉴赏基础薄弱的国内,试图让已经学成定型的舞者理解现代舞与人的内心、情绪、生命力产生的关联有多么美妙,这件事并不容易,但正好,做这件事能让辛颖与现代舞继续相处下去,继续产生关系。
她身上的力量感来自于此。
那天直到结束,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位说到兴起还会现场演示动作(收缩、后转、伸展)的女士已有身孕,面前的这个人仿佛与这些动作被糅合在了一起,像窗外呼呼闪动的树叶一样,随风吹而动。